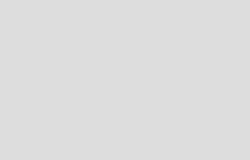为基辛格立传:我已经竭尽全力了
给一个人立传,不仅要按时间顺序讲述他生活中所有最重大的事件,还要把他私下的所书、所言、所想糅合在一起,除此以外,我实在无法想象还有更完美的写法。只有这样,大家才能仿佛看到一个活生生的人,与他“在其人生的每个场景同呼吸”,像他那样真切地经历人生的几个阶段……斗胆说一句,你对本书传主的了解将会比对其他任何在世的人都全面、深刻。而且你对他的了解会一如其人,因为我声明我写的不是颂词,必须歌功颂德,我写的是他的生活……每一幅画有光也有影。
——博斯韦尔(boswell),《约翰逊传》(life of johnson)
撰文 | 尼尔·弗格森
●●●
按照詹姆斯·博斯韦尔的理解,传记作家的任务就是让读者借他之眼看到一个活生生的传主。要做到这一点,传记作家必须了解传主。那就是说不仅要读别人勾勒传主生平的大量作品,还要阅读传主本人所写的全部作品。还有一层意思是,如果传主还健在,作家不仅要采访他,还要结识他,就像博斯韦尔结识约翰逊一样:跟他谈话,陪他吃饭,甚至结伴旅行。
当然,这里有一个难题:既要结识传主,又不能受其影响太深,否则,你说你写的是他的生活,而不是颂词,读者是不会相信的。博斯韦尔对约翰逊的敬爱也是慢慢培养起来的,他的《约翰逊传》之所以写得好,无外乎两点:一是写出了约翰逊举止粗鲁、不修边幅,二是(如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所言)把自己写得很滑稽—约翰逊睿智,而他却直接浅白;约翰逊是英国人,呆板乏味,而博斯韦尔是苏格兰人,过于急躁。我的做法有所不同。
本书在写作过程中得到了很多人的帮助(在致谢中已提到),除此以外,本书作者跟以往的传记作者相比有一个显著优势:我有幸查阅了基辛格的私人文件,不仅有他从政以来的文件(藏于美国国会图书馆),还有他2011年捐给耶鲁大学的私人文件,那些私人作品、书信和日记时间跨度极大,最早的可追溯到20世纪40年代,共计100多箱。我还对传主做过多次长时间专访。这本书不仅在写作时得到了基辛格的配合,而且其本身就是在他的授意下写就的。
正因如此,我料定一些心怀叵测的评论家会声称,我在某种意义上受到基辛格的影响或诱导,想给传主画一幅阿谀奉承的假画像。其实不然。尽管我得到允许,可以查阅基辛格的文件,也有人帮助我安排去采访他的家人同事,但我的唯一信念是在充分研究记录资料及其他可用证据的基础上,“竭尽全力去‘如实’记录他的一生”。我与基辛格在2004年签订了一份法律协议,协议里提到我的信念,最后一条是这样的:
虽然本作品的权威性会因为得到授权人(基辛格)的大力帮助而提升……(不过)更能提升其权威性的是作者的独立性;因此,双方理解并同意……作者全权编辑本作品定稿,授权人无权审查、编辑、修改本作品终稿,也无权阻止本作品的终稿出版。
只有一个例外:应基辛格博士的请求,我不能引用带有敏感个人信息的私人文件内容。我很高兴地说,他只在有限的几处行使了他的权利,每次都是跟纯粹的个人事务有关:其实是跟家庭事务有直接关系。
►基辛格
自开始撰写本书迄今已逾十载。岁月漫漫,痴心不改,我立志写一部“实实在在的”基辛格传记,用德国历史学家兰克的话说就是“如实直书”。兰克认为历史学家的职责就是从文献中推测历史真相—不是十几种文献(有一部被广泛传阅的基辛格传记引用的文献总共才十几种),而是成千上万种。我自然无法数清我和助手贾森·罗基特在本书写作过程中查阅了多少档案资料,只能清点我们认为值得纳入自建数字数据库的文件有多少。目前共有资料8 380种,合计37 645页。但是这些文献不仅仅取自基辛格的个人和公共文件。总之,我们引用的材料出自世界各地的111个档案馆,有重要的总统图书馆中的文件,也有默默无闻的私人收藏者的藏品。当然,有些档案一直是保密的,有些文件一直是机密的。相较而言,20世纪70年代的重要资料在数量上首屈一指。那个时代已经有了复印机和磁带录音机。有了复印机,各个机构很容易就把重要文件复制多份,这样,将来的历史学家就更有可能看到其中的一份。尼克松和基辛格钟情于录音机,加上“水门事件”后新闻自由进一步发展,许多本来绝不可能被记载的谈话,现在谁都能自由阅读。
我搜集材料时把网撒得尽可能又广又深,动机很明确。我决定不光从基辛格个人的角度看他的一生,还要从其他多个角度看他的一生,不光从美国角度来看,还要从朋友、敌人和中立者的角度来看。基辛格其人位高权重,说他在世界范围内纵横捭阖并不为过。为如此奇人立传必须要有全球视野。
对于这部传记,我一直以来都想写上下两部。问题是在哪里断开。最终我决定,上部就写到当选总统尼克松刚刚对世界宣布基辛格即将担任国家安全顾问之后、基辛格进驻白宫西翼地下室履新之前。这么划分有两点理由。其一,1968年年底,基辛格45岁,而我写本书时他91岁。所以,这一部差不多恰好涵盖他的前半生。其二,我想明确区分作为思想家的基辛格和作为行动者的基辛格。不错,1969年以前的基辛格不仅仅是一位学者。20世纪60年代那整整10年间,基辛格身为总统顾问和总统候选人顾问,直接参与了外交政策的制定。至少到了1967年,他已经积极参与外交事务,开始与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谈判,期望结束越南战争。但是,那时他还没有任何执政经验。他只是一名咨询师,还不是真正的顾问,更谈不上是决策者。事实上,美国前总统艾森豪威尔正是出于这个原因而反对新总统任命他为国家安全顾问。听说尼克松要任命基辛格后,艾森豪威尔抗议道:“基辛格是个教授,你可以让教授做研究,但绝不能让他当什么官……我要给迪克打电话劝劝他。”基辛格的确是先当教授,后来才成为政治家的。所以,我以为1969年以前对他如此定位比较在理:美国历史上最重要的外交政策理论家之一。如果基辛格没有从政,这部传记仍然值得一写,就好比如果凯恩斯没有离开剑桥大学校园去执掌英国财政部,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照样有充足的理由写一部漂亮的凯恩斯传记。
博斯韦尔首次见到约翰逊是在伦敦的一家书店里。我和基辛格的第一次邂逅也是在伦敦,是在康拉德·布莱克举办的一次聚会上。当时我是牛津大学的一名教师,教点儿新闻学,这位老政治家说很佩服我写的一本有关“一战”的书,我自然受宠若惊。(还有一点也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名模艾拉·麦克弗森一进屋,他立马撇下我迎了上去。)几个月以后,基辛格授意我为他的传记执笔,我很开心,但更多的是惶恐。我很清楚,他曾找过另一位英国历史学家写传记,那个人也接受了,后来却临阵退缩。当时,我只能看到不接受这份苦差的理由:我手里有几本书(包括另一部传记)的合同、我不是研究战后美国外交政策的专家、我需要一头扎进浩如烟海的文献、我难免要遭到克里斯托弗·希钦斯等人的严厉抨击。为讨论写传记的事,我们见过几面,打过几次电话,通过几封信,但在2004年3月初,我还是回绝了。这也就拉开了我介绍亨利·基辛格外交艺术的序幕:
太遗憾了!收到你来信的时候,我正在到处找你的电话号码,打算告诉你,我找到了原以为散佚的文件:一名管理员保存在康涅狄格州一个储藏室里的145箱文件,文件保存下来之后那个人就死了。里面有我所有的文件:作品、书信、断断续续的日记,至少是1955年以前的,有可能是1950年以前的,还有约莫20箱我从政以来的私人信函……
尽管如此,经过多次交谈,我承认中间也犹豫过,但我相信,你一定能对我做出一个明确的、不一定是积极的评价。
因此我感谢你,尽管我深感遗憾。
几个星期之后,我来到康涅狄格州的肯特镇翻阅文件。
然而,说服我写这部传记的是那些文件,而不是文件的作者。那些我曾看过的文件至今还令我记忆犹新。基辛格在1948年7月28日的一封家书中写道:“我觉得事情不只分对与错,还有很多中间地带……生活真正的可悲之处不是在对与错之间选择。只有最无情的人才会明知是错的,还偏偏去做。” 麦乔治·邦迪于1956年2月17日给基辛格写了一封信:“我常想,哈佛会给她的儿子们(那些本科生)一个机会,让他们被自己喜欢的东西所塑造。这个机会,你这个哈佛学子得到了。对教职工来说,哈佛却只给了他们这样一个机会—一个危险的、也许是致命的机会,去受他们所痛恨的对象的影响。” 弗里茨·克雷默于1957年2月12日给基辛格写了一封信:“现在情况好些了。你只需拒绝野心家面临的那些完全平常的诱惑,比如贪婪,以及学术上的好奇心。注意这种诱惑是你自己性格中固有的。正在引诱你的……是你内心最深处的原则。”有一则日记写的是1964年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我们离开的时候……一个戈德华特的支持者一一核对了名单上的名字。上面没有我的名字。但他认识我,说‘基辛格,别以为我们会忘记你的名字’。”1965年秋访问越南的一则日记这样写道:“(克拉克·)克利福德后来问我怎么看总统的立场。我说我非常同情总统遭遇的困境,但是眼下危急的事是美国未来的世界地位……克利福德问我救越南人值得不值得。我说这个问题已经不存在了。” 我越看这些东西越感到别无选择,这部书我必须写。十多年前,我头一天到伦敦罗斯柴尔德档案馆查阅档案的时候非常兴奋,这种感觉现在又回来了。
因此,本书可谓十年爬梳、呕心沥血的成果。在写作过程中,我信守伟大的历史哲学家r. g. 科林伍德的三个观点。
1. 所有历史都是思想史。
2. 历史知识是研究思想史的历史学家对思想的再现。
3. 历史知识是对当前思想环境下蕴藏的过去思想的再现,当前的思想与过去的思想针锋相对,从而将后者局限在一个不同的层面上。
为了力图再现基辛格及其同代人过去的思想,我几乎总是偏重当时的文件和录音,而不是多年后采访中的证词,这不是因为文件总能准确记录作者的思想,而是因为记忆一般比信件、日记和备忘录更容易捉弄人。
然而,传统历史学家的研究方法也有局限性,无论他是一个多么具有批评精神的读者,更遑论他要记述的传主的根本特征之一是(或据说是)神秘莫测。这一点我稍做说明。写完第20章—这章讲的是基辛格找到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驻巴黎代表马文保,想通过他与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开始谈判,最终谈判流产—之后,过了几个星期,我和基辛格夫妇共进晚餐。这一章是全书到目前为止最难写的一章,很多人不明白约翰逊政府提出的秘密和平计划为什么代号是“宾夕法尼亚”,但我自认为把这个问题交代清楚了。我想我说明了一点,这位新上任的外交家居然甘愿(尽管他以前在学术上对此事进行过严厉批评)沦为自己谈判的俘虏,对事情一拖再拖,落入河内的圈套。越南民主共和国官员所说的谈判只是一种策略而已,实则另有所图,他们只是希望能阻止美国空袭其主要城市,若无果,至少也希望空袭能有所减少。
基辛格夫人本来没打算和我们一起吃饭,她突然在我身边落座,这让我吃了一惊。她问了个问题,中间还顿了顿。她问我:“你以为亨利老往巴黎跑,真正的原因是什么?”
我压根儿没想到(因为哪里也找不到相关记录)基辛格1967年去巴黎的主要原因是她那年在巴黎大学念书。
基辛格与第二任妻子的关系史可能要引起所有传记作家的警觉,尤其是为基辛格立传的作家。沃尔特·艾萨克森认定基辛格与南希·马金尼斯初次见面是在1964年旧金山举行的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这一点是对的。但是据艾萨克森记录,基辛格在担任尼克松的国家安全顾问期间,简直就是一个不为人知的“多情种子”,艾萨克森认为她不过是基辛格“见面最频繁的女友”。他的书有一章专写基辛格的“名气”,列举了基辛格在20世纪70年代初交往的女性,除了南希·马金尼斯之外,至少还有12个。
艾萨克森是对的,其他记者没有报道这件事。1973年5月28日以前,《纽约时报》压根儿就没提到南希·马金尼斯的名字,而当时她和基辛格已经认识9年了。1973年5月28日,《纽约时报》报道她(说她是“经常陪伴基辛格博士的人”)负责安排好在殖民地俱乐部举办的基辛格的50岁寿宴(她是该俱乐部的会员);4个月后,在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举行的联合国外交使团招待宴会上,马金尼斯又作为基辛格邀请的嘉宾出席。一位国务卿发言人告诉《纽约时报》记者,“她不过是普通嘉宾,不是女主人”。1973年12月21日,基辛格的另一位发言人“坚决否认”基辛格要与南希·马金尼斯结婚。1974年1月3日,基辛格本人婉言拒绝“对我的个人计划做出任何评价”。第二天,有人发现他们俩和别人共进晚餐,这个人正是《华盛顿邮报》的东家,这家报纸很快刊出基辛格否认两人打算结婚的声明。后来,有人看到他们两人观看了一场冰球赛,与时任美国副总统的杰拉尔德·福特出席了一次鸡尾酒会。尽管如此,两人于3月30日结婚的消息还是让媒体大跌眼镜。实际上,基辛格当天参加完记者招待会就直奔婚礼现场,在记者招待会上他对个人生活连半个字儿都没有透露。婚礼之后两人乘坐飞机去阿卡普尔科度蜜月,飞机起飞后半小时媒体才公布了他们的婚事。《华盛顿邮报》愤愤不平地报道:
这对新人急切地要避人耳目,一位记者看到他们离开国务院,打算过去采访,被一名身着制服的保安强行制止。保安拿走记者的出入证,抄下上面的信息后才还给她。基辛格的一名助手早已把车开了过来,防止任何人从地下停车场尾随这对新人。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华盛顿邮报》正一马当先、大张旗鼓地揭露一个更大的秘密:尼克松的水门丑闻!
不过,基辛格的第二次婚姻之所以神神秘秘,不能仅仅归因于“有教养的女士当然会厌恶张扬”。其中也有基辛格的原因,正是因为他,两人近10年的关系才一直是一个纯私人问题。要了解个中缘由,给他立传的人需要具备一种知识,一种无法在档案文件中找到的知识:要了解他内在的、大多未诉诸文字的生活,要了解他在生活中的多重身份:儿子、哥哥、情人、丈夫、父亲、离异者。此外,要了解基辛格夫妇怎么能长期保持隐私不曝光,写传记的人必须了解当时新闻媒体与政界名流之间依然是有默契的。事实上,无论是媒体大亨,还是华盛顿记者,对基辛格和马金尼斯的关系都了如指掌,知道两人基本上每两周就会有一个周末待在一起,不是在纽约就是在华盛顿。只不过他们心知肚明但不报道而已。
写传记的人中没有谁能做到无所不知,因为你不可能什么都知道,连传主本人也不是无所不知的。毋庸置疑,我遗漏了一些重要事件,误解或者低估了一些人际关系,有些想法根本就没记下来,当初有这些想法的人现在也忘了。但即便如此,我已经竭尽全力了。我这个基辛格的博斯韦尔做得好不好——在多大程度上避免了那个陷阱,还请诸君明断。
本文节选自《基辛格:理想主义者》,中信出版集团,2018年04月出版。文章标题为编者所加。
制版编辑:杨枭 |